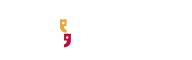專題文章:習得無助感:從實驗室到心理健康的深刻洞察
次閱讀
習得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是當個體在重複經歷無法控制的負面事件後,即使面對可控制的情境,也選擇放棄嘗試,表現出被動和無助的狀態。
習得無助感:從實驗室到心理健康的深刻洞察
習得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是一個在心理學領域中極為重要的概念,它描述了一種當個體在重複經歷無法控制的負面事件後,即使面對可控制的情境,也選擇放棄嘗試,表現出被動和無助的狀態。這種現象不僅深入探討了人類行為和情緒的底層機制,也對我們理解憂鬱症、焦慮症等心理健康問題提供了關鍵的視角。
最初的心理學實驗:Seligman與Maier的電擊實驗
習得無助感概念的誕生,要歸功於美國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和史蒂文·邁爾(Steven F. Maier)在1960年代對狗進行的一系列經典實驗。
實驗背景與設計:
在當時,行為主義心理學盛行,研究者多半關注刺激-反應的連結。然而,塞利格曼和邁爾對巴甫洛夫的古典制約理論產生了疑問,他們想知道動物是否會在經歷了無法控制的厭惡刺激後,仍然能學會逃避。
他們設計了一個巧妙的實驗,將狗分成三個組別:
可逃脫組(Escapable Shock Group): 這組狗被放置在一個特殊的籠子裡,籠子地板會傳導輕微的電擊。然而,籠子內有一個隔板,狗可以跳過隔板到達另一邊,從而避開電擊。這些狗很快就學會了跳過隔板來停止電擊。
不可逃脫組(Inescapable Shock Group): 這組狗與可逃脫組的狗通過一個特殊的裝置連接,牠們也會受到與可逃脫組相同頻率和強度的電擊。然而,無論牠們做什麼,都無法停止電擊。也就是說,電擊對牠們而言是不可控制的。
控制組(No Shock Control Group): 這組狗沒有受到任何電擊,僅作為對照組。
實驗結果:
在第一階段的實驗結束後,研究人員將所有狗都帶到另一個新的實驗裝置中,這是一個穿梭箱(shuttle box)。這個箱子中間有一個低矮的隔板,電擊會先從箱子的一邊開始,幾秒後,電擊會轉移到另一邊。狗只要學會跳過隔板,就可以避免電擊。
結果發現:
可逃脫組和控制組的狗: 牠們很快就學會了在電擊開始前或開始後立即跳過隔板,成功逃避了電擊。牠們展現出積極應對的能力。
不可逃脫組的狗: 大部分狗在電擊開始後,即使面對新的、可逃避的環境,牠們也只是被動地趴在地上,發出哀嚎,卻不嘗試跳過隔板來逃避電擊。即使電擊持續,牠們也表現出明顯的放棄行為。這正是習得無助感的最初表現。
這個實驗的突破性在於,它證明了個體在經歷了無法控制的負面事件後,即使面對可以控制的狀況,也會因為過去的「學習」而放棄嘗試。這顛覆了當時行為主義的許多觀點,並為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重要的實驗進程與理論發展
塞利格曼和邁爾的開創性研究引發了心理學界對習得無助感的廣泛關注,隨後數十年間,眾多研究者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量的實驗和理論拓展,使得習得無助感的概念日益完善。
1. 人類實驗的拓展
最初的實驗對象是動物,但研究者很快將目光轉向了人類。在1970年代,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們設計了針對人類的類似實驗,例如使用噪音作為厭惡刺激。
噪音實驗:
不可控制噪音組: 參與者被暴露在間歇性、不可控制的巨大噪音中,他們無法關閉噪音。
可控制噪音組: 參與者也能聽到噪音,但他們可以透過某種方式(例如按下按鈕)來停止噪音。
控制組: 沒有噪音。
在後續的測試中,當所有組的參與者都被置於一個可以透過簡單操作來停止噪音的環境時,那些先前經歷過不可控制噪音的參與者,往往表現出較低的解決問題的意願和能力,即使他們知道存在解決方案。他們更容易表現出沮喪、放棄的態度。
這些人類實驗進一步證實了習得無助感在人類身上的普遍性,並為理解人類的憂鬱、焦慮等情緒狀態提供了實驗依據。
2. 歸因理論的引入與習得樂觀主義
習得無助感最初的解釋偏向行為學派,認為是個體學會了「無助」的行為反應。然而,隨著認知心理學的興起,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們意識到,單純的行為解釋並不足以完全解釋這種複雜現象。他們引入了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特別是歸因風格(Attributional Style)的概念,為習得無助感提供了更深層次的認知解釋。
歸因理論的發展:
根據歸因理論,人們對於事件的發生會進行解釋,這些解釋方式會影響他們的情緒和行為。歸因風格主要有三個向度:
內部vs.外部(Internal vs. External): 是將失敗歸因於自身原因(如能力不足),還是外部原因(如運氣不好)。
穩定vs.不穩定(Stable vs. Unstable): 是將原因視為持久不變的(如性格缺陷),還是暫時性的(如一時失誤)。
全面vs.特定(Global vs. Specific): 是將失敗的原因擴展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我什麼都做不好」),還是僅限於特定情境(如「這項任務我沒做好」)。
悲觀的歸因風格(Pessimistic Attributional Style): 當個體傾向於將負面事件歸因於內部、穩定、全面的原因時(例如:「這是我能力不足造成的,我總是很差勁,而且在所有事情上都如此」),他們更容易發展出習得無助感,因為他們認為負面事件是無法改變且會影響所有領域的。
樂觀的歸因風格(Optimistic Attributional Style): 相反地,將負面事件歸因於外部、不穩定、特定的原因(例如:「這次失敗是因為運氣不好,下次會更好,而且這只影響這件事」),則有助於抵抗習得無助感。
基於歸因理論的深入,塞利格曼進一步發展出了習得樂觀主義(Learned Optimism)的概念。他認為,如果悲觀的歸因風格是習得的,那麼樂觀的歸因風格也可以透過學習和訓練來獲得。這為心理治療和個人成長提供了新的方向,強調透過改變思維模式來提升心理韌性。
3. 神經生物學基礎的探索
隨著腦科學和神經科學的進步,研究者開始探究習得無助感的神經生物學基礎。他們發現,長期暴露於不可控制的壓力源會導致大腦中某些區域的功能改變,特別是與情緒調節、壓力反應和決策相關的區域。
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 特別是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被認為在調節情緒和壓力反應中扮演關鍵角色。研究發現,在習得無助感的動物模型中,mPFC的活動可能受到抑制,導致其無法有效抑制杏仁核(amygdala)等恐懼相關腦區的活動。
杏仁核(Amygdala): 作為情緒處理的核心區域,杏仁核在習得無助感的形成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持續的、不可預測的壓力會導致杏仁核過度活躍,使得個體更容易產生焦慮和恐懼反應。
海馬迴(Hippocampus): 參與記憶和情緒調節。長期壓力可能導致海馬迴萎縮或功能受損,影響個體學習和應對新情境的能力。
神經傳導物質: 多巴胺、血清素、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等神經傳導物質的失衡也與習得無助感和憂鬱症的發展密切相關。例如,多巴胺系統的功能障礙可能導致動機降低和快感缺失。
這些神經生物學的發現,為習得無助感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釋,將心理層面的問題與大腦功能連結起來,為藥物治療和神經調節技術的應用提供了理論基礎。
4. 習得無助感與壓力模型
習得無助感與壓力應對模型也緊密相關。當個體面對壓力時,通常會採取兩種應對策略:
問題導向應對(Problem-focused Coping): 積極嘗試改變或解決壓力源。
情緒導向應對(Emotion-focused Coping): 試圖管理由壓力引起的情緒反應。
習得無助感的個體往往傾向於放棄問題導向應對,轉而採取被動的情緒導向應對,例如逃避、退縮或否認。這種被動的應對模式,長期來看,會加劇其無助感和負面情緒。
習得無助感與心理健康、精神疾患的最新研究
習得無助感作為一個解釋負面心理狀態的核心概念,近年來在SCI和SSCI期刊上持續有大量研究發表,特別是與憂鬱症、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以及其他精神疾患的關聯。以下是一些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發現:
1. 習得無助感與憂鬱症(Depression)
憂鬱症是與習得無助感關聯最密切的精神疾患。最新研究持續深入探討兩者的神經生物學機制、認知過程以及干預策略。
神經迴路異常: 多項研究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等技術,揭示了憂鬱症患者在面對不可控應激源時,其內側前額葉皮質(mPFC)和腹側紋狀體(ventral striatum)的功能異常。mPPC與情緒調節和決策有關,其功能低下會削弱個體從負面經驗中學習並採取行動的能力;腹側紋狀體則與獎勵和動機有關,其功能障礙會導致快感缺失和動機不足,這些都是習得無助感和憂鬱症的核心症狀。
例如,一篇發表在《Molecular Psychiatry》的研究發現,長期壓力會導致小鼠mPFC神經元活動的改變,使其表現出類憂鬱行為,而這些改變與習得無助感的形成有關。
認知偏誤與歸因風格: 憂鬱症患者普遍存在悲觀的歸因風格,他們傾向於將負面事件歸因於內部、穩定和全面的因素。近期研究進一步探討了這種歸因偏誤的神經認知基礎,發現其可能與大腦獎勵回路和認知控制能力的缺陷有關。干預研究也表明,透過認知行為療法(CBT)改變悲觀歸因風格,能有效緩解憂鬱症狀。
早期創傷經歷: 許多研究指出,童年期的逆境、虐待或忽視等早期創傷經歷,會顯著增加個體在成年後發展習得無助感和憂鬱症的風險。這類經歷可能改變大腦的壓力應激系統,使其對後續的壓力源更為敏感,更容易陷入無助的模式。
生物標誌物: 一些研究正在探索習得無助感和憂鬱症的生物標誌物,例如皮質醇水平、炎症因子、基因多態性等,以期能更早地預測和診斷。
2. 習得無助感與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s)
雖然憂鬱症是習得無助感最典型的表現,但焦慮症,尤其是廣泛性焦慮症(GAD)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也與習得無助感有著密切的聯繫。
不可控性與焦慮: 焦慮症的核心特徵之一是對不可控事物的過度擔憂。當個體長期處於無法預測和控制的威脅下時,會產生持續的焦慮感,並最終可能發展出習得無助感。例如,廣泛性焦慮症患者常會對各種日常事件產生過度且難以控制的擔憂,即使這些事件在客觀上是可控的。
PTSD與創傷: 在PTSD患者中,創傷經歷本身就是極度不可控的事件。研究顯示,那些在創傷事件中感知到更高程度無助感(例如,無法逃脫、無法反抗)的個體,更容易發展出PTSD。他們可能因此對世界產生一種「不可預測且危險」的信念,導致迴避行為和情感麻木,這正是習得無助感的表現。治療PTSD的策略,如暴露療法,其原理之一就是幫助患者在安全環境中重新獲得對創傷記憶的控制感,以打破習得無助的循環。
神經影像學證據: 對於焦慮症患者,研究發現其杏仁核(處理恐懼和焦慮)過度活躍,而與認知控制和情緒調節相關的前額葉皮質功能相對低下,這與習得無助感的神經機制有重疊。
3. 習得無助感與其他精神疾患及行為問題
習得無助感的概念也被應用於解釋其他多種精神疾患和行為問題:
物質使用障礙: 部分研究認為,習得無助感可能促使個體轉向物質濫用,作為一種應對無力和絕望的方式,以暫時逃避負面情緒。
飲食失調: 在某些飲食失調患者中,對體重和食物的失控感,以及對自身控制能力的無助感,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慢性疼痛: 慢性疼痛患者可能因長期疼痛而感到無助和沮喪,這會導致活動減少、社交孤立,進而加劇疼痛體驗和憂鬱情緒。
學業失敗與職業倦怠: 在教育和組織心理學領域,習得無助感也用於解釋學生在學業上的屢次失敗後放棄努力,或員工在面對無法解決的工作壓力時產生職業倦怠。
4. 介入與治療策略
基於對習得無助感機制理解的加深,相關介入策略也日益精進。
認知行為療法(CBT): 仍然是改變悲觀歸因風格和提升應對能力的核心療法。CBT幫助患者識別和挑戰非理性的負面思維模式,並學習更具建設性的應對策略。
正向心理學干預: 塞利格曼作為正向心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強調透過培養個體的優勢、提升希望感、發展感恩和寬恕等,來預防和緩解習得無助感。這類干預旨在主動建立心理韌性。
神經調節技術: 隨著神經科學的發展,經顱磁刺激(TMS)和經顱直流電刺激(tDCS)等非侵入性神經調節技術,被用於調節與習得無助感和憂鬱症相關的大腦區域活動,顯示出潛在的治療效果。
基於正念的介入(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正念訓練強調活在當下,不帶批判地覺察自己的思想和情緒。這有助於個體擺脫對過去失敗的沉溺和對未來不可控事件的擔憂,從而減少無助感。
韌性訓練(Resilience Training): 許多心理健康促進計畫都包含了韌性訓練,旨在教導個體如何有效地應對逆境,增強其面對挑戰時的心理彈性,這直接對抗了習得無助感的負面影響。
習得無助感是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心理學概念,它從最初的動物實驗,逐步發展為解釋人類複雜心理現象的關鍵理論。從神經生物學的層面理解其形成機制,到結合歸因風格和認知過程解釋其與憂鬱症、焦慮症的緊密關聯,再到開發多樣化的干預策略,這些研究進展都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人類心理健康和精神疾患的認識。
理解習得無助感不僅有助於專業人士進行更有效的診斷和治療,也為普通人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即使面對困境,我們也並非完全無力。透過學習改變思維模式,培養積極的歸因風格,以及主動提升心理韌性,每個人都有機會擺脫無助的泥沼,重獲對生活的掌控感。這也正是心理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幫助人們過上更充實、更有意義的生活。
- publisher:
- 聊聊心理治療所
-